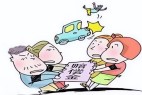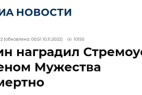交通事故中营运车辆停运损失的赔偿——从两省高院的不同判例谈起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中造成营运车辆受损,在事故处理期间及车辆修理期间车辆停运导致的预期利益的损失,虽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支持该损失,但实践中车辆保险公司对于此部分的损失“赔与不赔”有着相当大的争议。
关键词:营运车辆 保险公司 停运损失 赔付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承保机动车保险有2.6亿辆车,保费收入8189亿元,占整个财险保费的63%。这其中有大部分车辆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三者险。好多投保人对自己购买保险的赔付范围不大了解,发生交通事故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买了保险,应由保险公司代自己承担责任。事实上,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被保险人,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承担的责任应由保险公司代为清偿,包括为此支出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等,无论这些费用的多寡,保险公司对这些赔付项目基本没有异议。但除以上项目外,交通事故中对于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是否应由保险公司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大的争议,一些法院的判决在基于同样事实的基础上却做出完全不同的判决。本文主要就营运车辆停运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营运车辆停运损失在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这里先给大家解释下营运车辆停运损失的概念。停运损失就是由于事故导致营运车辆暂不能营运,在合理的事故处理及车辆修理期间预期收入的减少。
查询权威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会发现各地法院的裁判观点各不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法院认为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属于交通事故的直接损失(或不属于间接损失),判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比如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7民终665号、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5民终687号裁判文书;有的法院认为,停运损失是交通事故的间接损失,如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6民终4905号、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5民终233号裁判文书等。在这些持间接损失的判例中,有的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单等证据,认为保险公司未尽到合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所以保险公司应承担赔付责任,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再38号判决书;有些法院则认为保险公司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所以判决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车辆停运损失,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申1095号裁定书。
有意思的是,如果认真比较上述山东高院与陕西高院的两个案例,就会发现两个案例的事实情况基本相同,都是投保人是公司法人,办理保险业务时在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或保险提示单上加盖了公章,陕西高院审理法官认为投保人在保险提示单上加盖了公章,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与说明”义务,所以保险公司不应赔偿停运损失;同样的事实,山东高院审理法官则认为,虽然投保人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加盖了公章,但未有经办人的签名,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了“说明”义务,所以判决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停运损失。
至此大家会发现,在事实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两个省的高院审理法官却持不同的观点,做出了结果完全不同的判决或裁定。根据相同的法律规定,两个省的高院审理法官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定,在基本事实相同的情况下,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更别说各省基层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了。
二、停运损失同案不同判的原因
(一)、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营运车辆停运损失
之所以出现上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停运损失损失是否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承担,不像事故中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等事故损失,已在交强险条款中明确规定由保险公司承担。这就是为什么司法实践中,其他赔偿项目基本没有争议,而唯独“停运损失”却出现如上所举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权威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同样案例出现不同判决结果,这会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
(二)、因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官只能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定做出自由裁量
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设置了极具争议的格式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从这个条款中可知,保险公司对于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所造成的“停驶”损失(对于营运车辆就是停运损失)不予赔偿。这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但该免责条款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就要根据具体法律规定及保险公司收取保费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从这两条法律规定可得出这样的判断:一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提请另一方注意并按要求予以说明;二是该免责条款是不是“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条款。司法实践中,因为保险公司将“停驶”和其它比较合理的免赔情形,如“停水、停电、停气”等一并列举,设置在一个条款中,法院很难认为上述保险条款因显失公平而无效,所以只能要求保险公司对这样的条款给投保人应予以提示和说明。
另外,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为了在实践中能更好地施行该条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又对此专门做出了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在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至此,读者可能应该能理解为什么陕西高院与山东高院就基本相同的事实却做出了结论完全相反的认定,说白了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根据自身的经验及认识(还有可能是本省的通行作法),来判断保险公司究竟是否履行了法律所要求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而此种判断没有客观标准,完全出自法官的自由裁量,就像上面陕西高院和山东高院的判例,陕西高院的审理法官认为投保人“保险提示单上盖章”,保险公司已尽到了义务;而山东高院审理法官认为,即使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但没有经办人的签名,保险公司未尽到义务,就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保险公司是否存在多收保费却又通过合同条款免责的不诚信行为
作为普通大众,尤其是购买了“全险”的投保人,觉得保险公司收了自己的保费,在事故发生后却因为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而拒赔,心理确实不服气,当然就抱怨保险公司不诚信了,这也是保险公司被大多数投保人经常诟病的原因之一。
问题的症结就是保险公司所收的商业三者险保费中是否包含了事故发生后导致对方“停驶”的因素。如果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在计算三者险保费时,已将事故发生后导致对方“停驶”的因素作为核定保费的因素之一,也就是保险公司所收的保费中含有事故发生后“停驶”的因素,就像包含了受伤人员的“误工费、护理费等”因素一样,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在此情形下的免责应为无效,保险公司对停运损失就应予以赔偿。保险公司不能一面收了投保人含有此因素的保费,另一面却通过格式条款将此因素的赔付免除,这是极不诚信的行为,严重损害投保人的权益,对于投保人则显失公平。如果能够证实保险公司存在此种现象,司法实践中法官可直接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认为这样的条款应为无效条款。
如果保险公司在核算保费时没有考虑“停驶”的因素,即所收的保费不含有这样的因素,法院才应该根据上述保险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做出具体的判决,这样对保险公司及投保人来说都公平。
但关键的问题是,由谁判断保险公司在核算保费时,是否考虑了“停驶”因素,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由银保监会等行业监管部门公开保险公司相关核算数据,作为普通大众的投保人,也就能更加明明白白消费。
三、对于解决此问题上同案不同判的几点建议
(一)、保险公司为了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应主动将“停驶”在相关免责条款中删除
大家都知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营运车辆的停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发生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点很多人都可理解,毕竟交通事故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极为罕见,但保险公司在制订条款时确实是煞费苦心,将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常出现的“停驶”情形,“隐藏”在与交通事故没有经常关联的诸多情形之中,除非是专业人士,或者保险公司人员在投保时就此专门进行耐心细致的提醒,一般普通大众很难发现这其中的猫腻。大多数投保人,只有发生交通事故遭到保险公司拒赔后,才知道买保险时曾有这样的条款。但即使有了这样的教训,在今后买保险时,即便投保人自己提出多交保费以享有这样的保障,保险公司也无法更改这样的条款。因为各保险公司的条款都是格式条款,作为消费者的投保人根本没有选择。
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几种免责情形中,“停驶”的几率很高,几乎双反事故中都存在造成对方车辆“停驶”的情形。而其它情形则极为罕见,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停水”“停电”“停气”等情形,肯定是有其它媒介参与后的间接损失,如事故撞断电线杆,导致工厂停电的损失;撞断水管,导致工厂停业的损失。这些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多数人可以理解。但事故发生后导致对方车辆的“停驶”损失,本身就是投保人购买此类保险的目的之一,暂不论此种损失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能以存在免责条款而拒赔。将交通事故发生后常见的“停驶”情形,与极为罕见地“停水”“停电”“停气”等情形并列在一个条款中而免责,保险公司的此种做法本身就极不诚信,对作为消费者的投保人也极为不公。
(二)、司法实践中应加大保险公司的举证责任,从而倒逼保险公司对此问题进行整改
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已经按法律的要求对免责条款中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给予投保人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要求保险公司要么通过录音录像,要么通过书面形式等,证明在投保人购买保险时已将类似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让其足以理解的说明义务,使投保人能够明明白白消费,从而减少发生事故后不必要的纠纷。如果这样办理保险手续,一个保单办下来将比保险公司现有的做法至少要多花费十分钟时间。但目前保险公司为了提高办事效率,通行的做法是,将免责条款用黑体字加粗,以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在投保人声明处,要求投保人签名,就尽到了“说明”义务。所以实践中保险公司为了省事,根本不给投保人进行说明,而是在提示单中只要求投保人签名就行,即使因此发生纠纷,法院一般认为在提示栏中有投保人的签名,保险公司已尽到了说明义务,从而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以后投保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办理保险时自己进行录音录像,以备不时之需。这样的做法是否社会成本太高。
从本文所举的山东高院和陕西高院的两个案例来判断,山东高院的分析就更进一步,法人单位在保险提示单上盖章后,还应要求在投保人声明处有经办人的签名,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这种判罚更有人情味,也更接近社会生活实际。所以从公平、诚信的原则以及证据分配规则来判断,还是山东高院的判决更有信服力。
(三)、最高院应针对此问题尽早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杜绝此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前面已经缠述,保险公司如果考虑了“停驶”的因素,而又将此种情形列入免赔的情形之中,对广大投保人就是极度的不公平,应该直接认为这个条款为无效条款。若没有考虑“停驶”的因素,也应该由保险公司详细举证,已完全尽到了法律所要求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公平,不要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判决结果,影响司法公正的公信力。
总之,随着国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案例裁判在网上公布,国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将极大地损害普通大众心目中的法律尊严,希望相关部门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完善制度,使公布的案例尽可能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